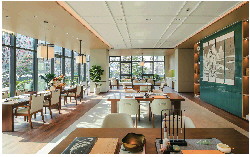
自信托行业“三分类”改革以来,资产服务信托成为信托业转型发展的主力,南宫28娱乐平台财富管理服务信托在“三分类”中居首位。在其中的19个业务品种中,特殊需要信托以其独特的定位和制度设计崭露头角,正处于理论与实践并行的发展阶段。
“2025年,中国信托业协会确立《我国特殊需要信托服务模式探究》专题研究课题,旨在研究我国特殊需要信托业务服务模式,为更好满足特殊需要人士的特定需求,提供有效信托服务供给。”课题组牵头单位华鑫信托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信托业特约研究员袁田告诉《金融时报》记者。
在业内人士看来,特殊需要信托是信托业充分践行金融政治性和人民性的体现。那么,特殊需要信托如何发挥信托本源功能,实现“为民所用”“为民所托”“为民所盼”?根据课题组的初步研究成果,袁田认为,我国特殊需要信托服务模式建设应立足服务对象、服务体系、服务规范、服务评价、服务价值五个维度展开,建立“管事、管钱、做事、监督”四位一体协同联动的服务机制。
一是明确界定服务对象。《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具体分类要求》对特殊需要信托已有定义,但业务实践对特殊需要信托的受益人范围理解并不统一。因失能失智而丧失对个人财产进行自主决策和管理是设立特殊需要信托的主要动因,特殊需要信托的“特殊”是指受益人应当具有特殊性,即为“特定受益人”,而非需求具有特殊性,这是判断特殊需要信托业务的起点。其一,当事人设立信托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可在合法合规边界内个性化设置,这是设立信托的自由。其二,失能失智人群的需求一般只是正常的生活需求,正是因为自身失能失智而无法得以满足,才需要设立信托助力,汇集更多服务资源保护受益人权益。
二是建立综合服务体系。开展特殊需要信托服务,需要处理好信托当事人与监护人、执行人、监察人的关系。对于失能失智等特殊群体,监护制度是对其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民事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重要法律制度,与是否设立信托本身并不相关。监护人能否对信托财产享有决策权以及决策权的内容和边界,取决于信托设立人的自愿安排,是否将其纳入信托关系。实践中,信托公司一般建议信托设立人将监护人设置为特殊需要信托的指令权人或保护人,更有利于其行使“管事”职责,以避免当设立人因身故或其他原因不在位时,对受益人生活照料的决策主体缺位,影响受益人利益和信托目的实现。
三是梳理服务规范。实现特殊需要信托的预期目的,是各类服务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信托合同和相关信托文件是各方基于共识的意定约束,除遵守信托合同和相关信托文件约定外,监护人、执行人、监察人还需要遵守各自领域的执业规范。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是承担受托责任的主体,须在信托法律及信托监管规则范围内,围绕信托财产管理即“管钱”边界内,履行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受托人对监护人的“管事”职责具有协助义务、对执行人的“做事”职责具有选任和监督义务、对监察人的“监督”具有配合义务,多元主体的多层次责任具有相对性,应建立并遵守多类型的服务行为规范,受托人、监护人、执行人、监察人须各司其职,多方协同,建立权责明晰的服务体系,共同维护特殊需要信托的有效运行,确保受益人合法权益最大化。
四是完善服务评价。特殊需要信托的业务实践正处于多样化创新尝试的发展初期,争取“首单落地”既是信托设立人的信任“破冰”,也是信托公司深化服务转型,实现品牌宣传效果的有力驱动。从促进特殊需要信托可持续健康发展、加快探索成熟商业模式角度,应同步建立可推广、可评价、可拓展的多类型试点模式。鼓励信托公司与各类相关主体合作创新,自主发挥做好“多选题”和差异化的解决方案。例如,因地制宜设置信托财产设立门槛,丰富信托财产现金及不动产等非现金形式,当事人协商合意确定信托费用及信托报酬标准,持续拓展康养机构、居家、社区等服务场景,个性化设计受托服务内容及流程。
五是提升服务价值。特殊需要信托的服务功能决定了其在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方面的重要社会价值,是夯实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的制度创新,可以兼顾当事人私益自治和社会公共服务融合。虽然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职责是对信托财产的安全审慎管理,但受托人是必要非充分角色,特殊需要信托是各类服务机构协同合作的平台,信托服务、保险服务、康养服务、监护服务、公益慈善服务都可以基于该平台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提供差异化服务。
今年7月末,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将对特殊困难群体的权益保护提升至更高层面。袁田表示,特殊需要群体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关注,各管理部门也需要探索监管协同新模式,引导监督各类相关主体规范服务,持续优化保障特殊需要群体的合法权益,共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